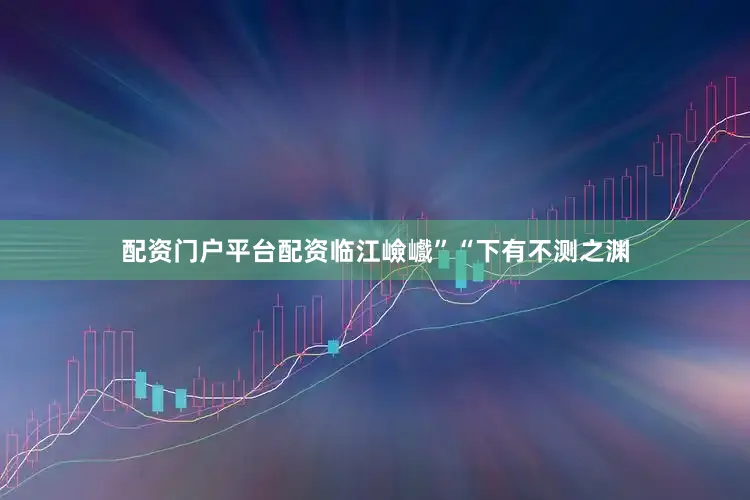
第二二一篇
书法经典钩沉·东汉书法·郙阁颂
被低估的巨人:《郙阁颂》如何颠覆我们对汉隶的想象
诗文/卢秀辉
《郙阁颂》歌
镂刻藏深峡,峥嵘陇蜀间。
摩崖春雨立,斧凿万千般。
太守兴徭役,析桥倾险关。
吏民怀德政,商旅破愁颜。
荒僻承鸿制,砂岩记厚顽。
纵横随嶂势,疏密应天悭。
双刃雕棱角,斜锋挫梗弯。
崩颓成锯齿,斑驳化纹环。
结字欹而正,构形迁亦娴。
逆波沉坠石,竖戟贯空山。
撇捺乱云聚,点钩星斗攀。
章华因利导,气韵共潺湲。
野性凌宗庙,浑沦藐末班。
隶楷穷变际,金匮肇开圜。
唐宋湮迷雾,明清出旧纶。
灵犀存断简,江岸遗苔虨。
拓本传神采,剜痕损辙䡲。
品评分优劣,考辨沥诚艰。
论艺须弘道,观书要思眅。
衰荣抛世运,显晦契时邖。
巨手虽残笔,精魂不可删。
今朝重审视,古雅待追还。
绝壁龙蛇走,沧浪日月闲。
惟怜真魄在,莫作急流矕。
再估汉碑史,凤凰岂轻肦。
前言
《郙阁颂》始终是书法史叙述中的“边缘角色”。然而,正是这种“边缘性”,赋予了它超越规整庙堂书风的野性生命力——没有碑碣形制的束缚,没有官方审美的规训,它以悬崖为纸、以凿刀为笔,将东汉隶书的厚重与山野的粗犷熔于一炉。它不仅是东汉隶书演化末期的“活化石”,记录着隶变向楷书过渡的关键痕迹,更是一部被石头封存的书法变革宣言,昭示着书法艺术突破规范、拥抱自然的另一种可能。本文将以《郙阁颂》为原点,深入其文本内核、材质特性、工艺细节与艺术肌理,探寻被常规书法史叙事遮蔽的真相,为汉隶艺术的多元解读补上关键一环。
悬崖上的纪功碑
《郙阁颂》全称《汉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桥郙阁颂》,刻于东汉建宁五年(公元172年),比《杨叔恭残碑》晚一年,同属灵帝时期的碑刻。其内容核心是记载武都太守李翕主持修建析里桥阁道的事迹,但这篇铭文绝非单纯的官样文章或歌功颂德之作,而是一篇融合工程纪实、地理叙事与政治修辞的复合文本,字里行间藏着东汉晚期地方治理的深层逻辑。
文中“析里桥阁,临江嶮巇”“下有不测之渊,上有悬崖之峭”等句,不仅精准描绘了蜀道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的天险环境——析里桥地处今陕西略阳,是陇蜀通道的咽喉,江水湍急、崖壁陡峭,自古便是交通难题——更暗含了汉代官吏对边陲交通治理的重视。在中央权威渐衰的东汉晚期,地方官吏的政绩不再局限于赋税征收或治安维护,“兴修基建、打通通道”成为巩固统治、惠及民生的关键举措。值得注意的是,碑文多次强调“百姓欢欣,商旅赞颂”“君子安乐,庶士悦雍”,看似是常规的颂赞之语,实则是将公共工程与民生经济直接绑定:桥阁道的修建,不仅解决了百姓出行难题,更打通了盐铁等物资的运输通道,让商旅通行更安全、贸易更顺畅。这种“基建即民生”的表述,折射出东汉中后期地方治理中“实用主义”倾向的崛起——相较于空洞的道德说教,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工程实绩,更能赢得民心与权威。
此外,碑文对工程细节的记载也颇具价值,如“造作桥阁,万世之基”“□□守节,非可禁防”等句,既点明了桥阁道的“长效价值”,也暗示了修建过程中的艰难。这种将“功绩”与“艰辛”并置的写法,让碑刻的纪功属性更显真实,而非一味夸大。可以说,《郙阁颂》不仅是一块书法碑刻,更是一份记录东汉晚期地方治理、经济交通与社会心态的“原始档案”,为我们理解其书法风格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语境。
隶变末期的社会镜像
《郙阁颂》的创作背景,深植于东汉晚期特殊的社会土壤,其书写者身份、书写动机,都与当时的政治格局、经济需求紧密相连,绝非偶然。
从政治维度看,灵帝时期的东汉王朝已显颓势:宦官与外戚争斗不断,中央政权内耗严重,对地方的掌控力逐渐减弱。在这种背景下,地方官吏反而成为实际治理的“核心力量”——他们手握行政、军事权力,既能主导地方基建,也能稳定区域秩序。武都太守李翕修建析里桥阁道,表面是“为民办实事”的政绩工程,实则暗含巩固地方权力的深层考量:通过解决交通难题,赢得百姓与商旅的支持,强化自身在陇蜀地区的权威;同时,打通陇蜀通道,也能加强与周边区域的联系,提升武都郡的战略地位。这种“以基建固权”的逻辑,是东汉晚期地方治理的典型特征。
而书写者仇靖(字子长)的身份更具深意。据碑文末尾“故吏仇靖字子长书此”的记载,仇靖是李翕的“故吏”,即曾在李翕手下任职的下级吏员。这一身份打破了“汉碑多出自名家之手”的刻板印象——事实上,汉代绝大多数碑刻,尤其是地方碑刻,均出自这类无名书吏之手。他们长期负责文书书写、档案记录,熟悉隶书的日常应用,是隶书“日常化”“地域化”的直接推动者。与庙堂碑刻的书丹者(多为文人或专业书家)不同,仇靖的书写更贴近“实用书写”的本质:不追求极致的精致与规范,而是以清晰、有力为首要目标,同时融入地域书写的习惯与个性。这种“非专业书家”的书写视角,恰恰是《郙阁颂》区别于《礼器碑》《乙瑛碑》等庙堂碑刻的关键——它没有刻意雕琢的“庙堂气”,反而多了几分自然随性的“山野气”。
从经济维度看,《郙阁颂》的诞生与蜀道沿线商贸活动的繁荣密不可分。东汉晚期,尽管中央政权动荡,但地方贸易并未停滞,尤其是陇蜀地区,因盛产盐、铁、丝绸等物资,成为重要的贸易枢纽。略阳作为陇蜀通道的关键节点,既是军事关隘,也是商旅必经之地。然而,险峻的蜀道始终是贸易的“绊脚石”——江水湍急、山路陡峭,货物运输困难且危险,商旅时常因交通受阻而蒙受损失。因此,修建一条安全、通畅的桥阁道,成为商旅群体的迫切需求。碑文中“舆徒欢喜,工力万计”一句,便暗含了商旅对通道开通的期待与喜悦。这种强烈的社会经济需求,解释了为何在偏远的悬崖上会出现如此规模的刻石:它不仅是为李翕纪功,更是对“资源控制与流通权力”的宣示——桥阁道的存在,意味着对陇蜀贸易通道的掌控,而碑刻的镌刻,则是将这种“掌控权”永久固化在石头上,让后世知晓这一功绩的归属。
石头的语言
《郙阁颂》与其他汉碑最直观的区别,在于其“摩崖”载体——它不是人工打磨的规整碑石,而是直接刻在天然崖壁上,这种材质与形制的差异,从根源上塑造了它的书法风格,堪称“石头的语言”。
其载体是一面天然砂岩崖壁,高约170厘米、宽约125厘米。砂岩的特性与洛阳、曲阜一带碑林常用的石灰岩截然不同:石灰岩质地坚硬、细腻,适合精细镌刻,能最大限度保留毛笔书写的细微笔触;而砂岩质地相对松软、颗粒较粗,易于下刀,但也容易因风化、水流侵蚀而受损。这种材质特性,决定了《郙阁颂》的书法必须“因地制宜”:书丹时无法像在平整石碑上那样追求精准的笔画位置,需根据石面的起伏、纹理调整笔触——石面凸起处,笔画可能略细、略短;石面凹陷处,笔画可能略粗、略长;甚至石纹的走向,也会影响线条的倾斜角度。这种“向自然妥协”的书写,让线条少了几分人工的精致,多了几分天然的粗犷,形成了“以天然残缺对抗人工完美”的独特美感。
刀与笔的共谋
汉碑艺术是“笔”与“刀”的结合,但《郙阁颂》的特殊性在于,刻工并非被动复制书丹痕迹,而是以“刀”为主动创作工具,对书法进行了二次重塑,形成了“刀笔共生”的独特面貌。
研究高清拓片可见,《郙阁颂》的刻工采用了独特的“双刀斜刻法”:刻工先在书丹笔画两侧刻出两道倾斜的刀痕,再剔除中间的石料。这种技法的特点是,刀刃入石角度较大(约45度),导致笔画边缘容易出现崩裂、剥落,形成粗犷的锯齿状效果。在传统碑刻审美中,这种“崩裂”可能被视为“工艺缺陷”——毕竟《礼器碑》《乙瑛碑》的刻工追求的是“刀随笔走”,让刀痕完全服务于笔意,尽可能隐藏刻凿痕迹;但在《郙阁颂》中,这种“缺陷”反而成为了风格的“亮点”:横画末端的波磔,因边缘崩裂而更显厚重,如同磐石般沉稳;撇捺的出锋,因石质剥落而增添朦胧感,不似庙堂碑刻那般锋芒毕露;甚至竖画的中段,也因颗粒状的石质而呈现出“毛糙”的质感,让线条更具张力。这种“以缺陷为美”的处理,让《郙阁颂》的书法脱离了“笔墨的流畅性”,转向了“金石的凝重感”,每一笔都像是用钝刃劈凿而出,带着山野的蛮力与沧桑。
更关键的是,刻工并非简单复刻书丹,而是进行了“以刀代笔”的二次创作。许多笔画的形态,明显是刻刀直接凿出的结果,而非毛笔书写的痕迹:例如“之”字的转折处,可见多层刀锋叠加的凿痕,不是毛笔圆转的弧度,而是刀凿的方硬棱角;“水”字的三点水,不是毛笔的轻盈点画,而是三个深浅不一的凿坑,呈三角形排布,更显厚重;甚至部分横画的起笔,没有毛笔藏锋的圆润,而是直接以刀斜切,形成锐利的方笔,如同斧劈刀削。这种“刀意盖过笔意”的处理,让《郙阁颂》的书法多了几分“刻凿性”,少了几分“书写性”——它不再是“石头上的毛笔字”,而是“用刀刻出来的书法”。这种“笔为刀服务”的创作逻辑,与庙堂碑刻“刀为笔服务”的逻辑截然相反,却恰恰成就了《郙阁颂》的独特风格:它不追求笔墨的细腻与流畅,而是追求刀凿的力量与质感,将书法的“软美”转化为“硬气”,成为汉碑中“金石味”最浓郁的作品之一。
图片
《郙阁颂》的艺术辩证法则
《郙阁颂》的书法艺术,核心是“野性”与“秩序”的辩证统一:看似粗野、随意的外表下,藏着严谨的笔法、结字与章法逻辑,这种“外乱内整”的特质,让它在汉隶中独树一帜。
从结体来看,《郙阁颂》看似笨拙、欹侧,实则暗藏精妙的平衡术。它不追求《熹平石经》那种绝对的对称、规整,而是以“动态平衡”为核心:许多字的部件看似高低错落、左右失衡,却能通过某一笔画的调整,达成整体的稳定。例如“继”字,左部“纟”旁略高,右部“糸”旁略低,左右部件呈倾斜之势,看似要“倾倒”,但右部最后一笔斜捺却顺势向下延伸,如同“秤砣”般稳住重心,让整个字在欹侧中恢复平衡;再如“渊”字,三点水并非垂直排列,而是呈弧形向上弯曲,右部“渊”的主体则略向左倾,与三点水的弧形形成“围合之势”,既化解了左轻右重的失衡感,又让结体多了几分灵动。这种“不正而正”“以奇求正”的结字法则,是《郙阁颂》对汉隶结体的重要突破——它打破了“对称即美”的常规思维,用动态的平衡替代静态的规整,让每个字都充满生命力,如同山野间的树木,虽不笔直,却扎根土壤、姿态自然。
从线条来看,《郙阁颂》的线条是“钝刃劈出的金石味”,兼具力量感与沧桑感。其线条以方笔为主,起笔多为露锋斜切,如“一”字的起笔,直接以刀斜入石面,形成锐利的方角,没有丝毫藏锋的圆润;收笔则常顿挫回顶,如竖画的收笔,不是顺势出锋,而是略作停顿后向上回顶,形成“枣核状”的节点,让线条末端更显厚重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“波磔”的处理——作为隶书的标志性笔画,多数汉碑(如《曹全碑》《杨叔恭残碑》)的波磔追求轻盈上扬,“雁尾”挺拔飘逸;而《郙阁颂》的波磔却反其道而行之,“雁尾”不向上扬,反而压抑为短促下沉的形态,如同磐石坠地,力量蕴含其中,不张扬却极具冲击力。这种“反波磔”倾向,绝非偶然,而是隶变末期的关键信号——它预示着隶书的波磔开始弱化,向楷书的“捺画”过渡,为后世楷书的形成埋下了伏笔。此外,线条的“毛糙感”也为其增色不少:因砂岩质地粗糙,刻出的线条边缘不光滑,呈细微的锯齿状,如同历经风霜的老树表皮,带着时间的沧桑。这种“不完美”的线条,比光滑细腻的线条更具质感,更能传递出山野的粗犷与力量。
从章法来看,《郙阁颂》的章法是“摩崖的空间诗学”,实现了“人工秩序”与“自然地貌”的完美融合。全文共21行,每行约27字,但实际排布毫无刻板之感:石面凸起处,字距略紧,文字“挤”在一起,却不显杂乱,反而形成视觉焦点;石面凹陷处,字距略疏,文字“松”开来,给人呼吸的空间;甚至出现字组堆叠的情况,如“衡夷”二字,因石面狭窄,几乎粘连在一起,却通过笔画的穿插避让,保持了可读性。这种章法不是“预先设计”的,而是“临场应变”的——书丹者与刻工根据崖壁的实际情况,随时调整文字的位置与大小,让文字与崖壁的每一寸空间都“严丝合缝”。这种“因地成文”的传统,对后世摩崖书法影响深远,如北魏《石门铭》、唐代《纪太山铭》,都继承了《郙阁颂》“与自然对话”的章法逻辑,成为中国书法中独具特色的“摩崖流派”。
褪色的辉煌
《郙阁颂》的命运,与其书法风格一样曲折——它曾因蜀道湮没而被遗忘,因金石学兴起而重获关注,又因现代工程而受损,其物质载体的变迁,本身就是一部微型的书法接受史。
唐宋时期,因蜀道线路的调整,析里桥阁道逐渐废弃,《郙阁颂》所在的悬崖也被淹没在荒草与江水之中,罕为人知。直至南宋,金石学家洪适在《隶释》中收录了《郙阁颂》的全文与释文,才让这块“悬崖上的碑刻”重新进入学界视野。洪适在书中称赞其“书体古雅,有汉隶风骨”,虽未过多展开,却为后世研究留下了重要线索。
明代是《郙阁颂》研究的重要阶段。此时,金石学逐渐复兴,学者开始实地寻访汉碑,《郙阁颂》的拓本也开始流传。但由于崖壁风化严重,明代拓本已显残泐——部分笔画因石质剥落而模糊,个别文字甚至完全缺失。即便如此,其独特的书法风格仍吸引了不少书法家的关注,如明代书法家赵崡在《石墨镌华》中评价其“结字古拙,有三代遗意”,将其与上古文字的质朴感相联系,可见其艺术魅力已突破时代局限。
清代是《郙阁颂》地位提升的关键时期。乾嘉学派推动金石学走向鼎盛,学者们对汉碑的研究从“文本考证”转向“书法赏析”,《郙阁颂》的艺术价值被重新发掘。阮元在《北碑南帖论》中,将其与《西狭颂》并称为“陇南双璧”,认为二者“皆具摩崖之雄健,补庙堂碑之柔媚”;包世臣在《艺舟双楫》中更是深入分析其笔法,指出“《郙阁》方笔沉厚,实开北魏书风之先”,首次将其与后世书法风格的演变关联起来。
1970年代,当地为修建公路,对《郙阁颂》所在的崖壁进行爆破,导致原石崩落江中,损毁严重。虽然后来文物部门从江中打捞起部分残石,但多数文字已残缺不全,无法还原原貌。如今存于陕西略阳灵岩寺的《郙阁颂》,实为残石拼合与后世剜刻的“混合体”——部分能辨认的文字保留了原刻风貌,而缺失的文字则由后人根据拓本补刻,补刻部分虽力求贴近原刻风格,却少了几分天然的粗犷与力量。这种“残缺与补全”的现状,让《郙阁颂》的“真实性”变得复杂,已非东汉原刻的完整面貌,而是层层历史创伤叠加后的“重构品”。
结语
《郙阁颂》的“野性”,源于摩崖载体的天然属性与刻工的刀凿力量——不迎合庙堂审美,不追求笔墨流畅,而是以砂岩的粗糙、凿痕的厚重,展现书法最本真的“力量感”。这种“野性”,打破了“汉隶必规整”的刻板印象,证明隶书在官方体系之外,还有着更自由、更多元的表达可能。它的“残缺”,则源于千年的风化与人为的损毁——文字的缺失、线条的模糊,非但没有削弱其艺术价值,反而增添了“想象空间”,让观者在残缺中品味历史的沧桑,在模糊中感受书法的张力。这种“残缺美”,是规整碑刻无法复制的,也是《郙阁颂》最独特的魅力所在。
传统汉隶史多以庙堂碑刻为核心,强调“规范”与“典雅”,却忽视了地方碑刻、摩崖刻石的价值。而《郙阁颂》说明:汉隶的演变,不仅发生在洛阳、曲阜等文化中心,也发生在陇蜀等边陲之地;不仅由文人书家推动,也由无名书吏、民间刻工创造;不仅追求“精致美”,也崇尚“自然美”。它连接了书写与镌刻、人工与天然、规范与自由,填补了汉隶史中“边缘叙事”的空白,成为重构汉隶多元谱系的“终极拼图”。
图片
卢秀辉山水作品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股票配资官网平台,睿新策略,嗨牛股票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股票按天配资”一名网友告诉红星新闻记者
- 下一篇:没有了







